早上十点,在朱家角安麓酒店前,张军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脸上仍有一丝困意,头晚工作到深夜,晨又早起,还未从晨酣中清醒过来。
20分钟后,再从休息室走出时,已经一脸神采奕奕。这大概是能够站上舞台之人的天赋和本能,当他们要面对观众时,要上台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抛开,能够呈现出超越自身能量的光彩。
《牡丹亭》园林版之后我就知道这关过了,可以了
安麓酒店就在课植园附近,张军的“园林牡丹亭”在这儿演了八年,今年是这个版本的告别季,它将暂别舞台,等待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更新的面貌来面对观众。“这个演出环境需要被修缮,很多设备已经很老旧了,对于表演者来说太艰苦了,都挤在一间非常小的休息室内。再说这部戏演了足足七年了,七年间我们的艺术观念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所以我想要再把它改进,使其更符合我今天的想法,再拿出来演。”
几年前,在《牡丹亭》园林版又一次准备开场前,突降大雨,所有人都等着张军做决定,要不要开演。张军走出去,观众席已经坐满了,在雨中等着开场,他说:“演吧。”“真的是内衣裤都湿透了”,那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出。“有时候这种艰苦会让表演的美感消失,所以我们未来会在园区做一些设备上的更新,可以支持一些极端天气情况下的演出。这需要时间,所以现在它要停一停,再等等。”
九年前,张军辞去上海昆剧团副团长一职,出来成立了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开始寻找在艺术上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他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伙伴来到朱家角——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想要尝试“不一样的昆曲表演形式”。从一个“双手不沾人间琐事”的昆曲艺术家到从零开始的创业者,阳春白雪时时与一切尘埃与繁杂牵连、碰撞,这全新的体验让张军感到难以适应,而人在走出舒适区的时候总是难受的。
新建的园林需要种植竹子,园区的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响和动静,而此时张军的团队正在园区彩排,这让本来就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的张军彻底崩盘,双方爆发了冲突。“我那时候已经濒临崩溃了,因为所有问题都是没有预料到的。原来在剧场演出什么都是现成的,工种都分得很细,我只需要专心排练就好了,但现在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庞杂,再加上这是我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个戏,觉得成败就在这一把了,所有的情绪都压得我心力憔悴。”一年后,张军回头去看了当时跟拍的纪录片团队制成的片子,在看片室哭得稀里哗啦。
好在《牡丹亭》实景园林版的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演出前所有的担心,疑惑和焦虑,在演出结束那一刹,在观众爆炸式的掌声中彻底消散,站在舞台最后一束收光里的张军释怀了之前所有的压抑。“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以后什么事儿都不怕了,我会更勇敢。”开演前三天,躺在医院挂着点滴的张军心里都还在嘀咕,后悔辞职出来自己折腾,“做这样一个破演出干嘛?看把自己整死了吧?如果演出要是不灵的话,过两天就歇了吧。”但是演出结束那一刻,张军在观众热烈的反应中知道,可以了,这关过了。
那时候,张军艺术中心的核心人员只有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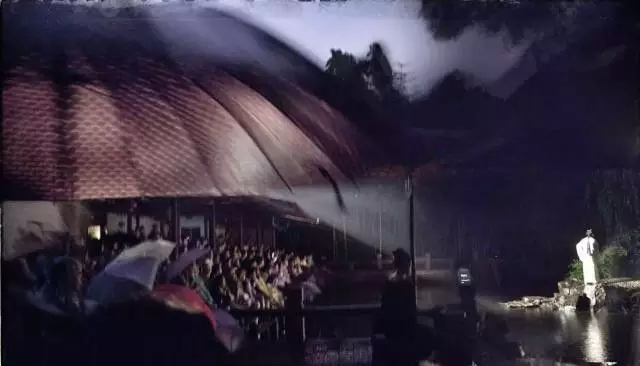
大雨中的“牡丹亭” 图片摘自@昆曲张军
昆曲,唱的是爱情,一定是要超越爱情演人心,就是要超越人心
2008年以前,唱了二十年小生的张军,在舞台上塑造过多少至情至性的角色,唱尽了情爱里的求不得,怨别离。但从小在戏校里接受的训练方式,让他谨遵老师传授的手眼身法步,唱小生就是小生样,唱柳梦梅就是柳梦梅,一招一式都是千锤百炼之后的样子,心里并无对戏以外更多的意识,对昆曲的理解也只是最基本的面貌。
2008年,谭盾为即将在阿姆斯特丹皇家歌剧院演出的《马可·波罗》作曲,邀张军来演出——用昆曲的唱腔来演绎西方的歌剧,这次跨界,对于张军日后的事业选择和对昆曲艺术的思考,起到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为了排演该剧,张军在阿姆斯特丹住了近半年的时间。“我那时候已经在上海昆剧团做副团长了,很多事都是惯性思维,一直在那个轮子里转,就会忽略很多东西。但我去阿姆斯特丹之后,反而跳出来了,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思考现状和创作,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大的反思空间。”
而第一次跟西方主流艺术团体合作,在完全不同的艺术语境中对话,东西方戏剧理念的碰撞给了张军恰逢其时的刺激。在《马可·波罗》中,他的角色是一个游记执笔者,是与马勒对话《大地之歌》的李白,还是庄子、影子,还是引领观众进入旅程的人……是提问者,也是解答问题的人。“这在我以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传统戏曲的人,演公子就是公子,演小姐就是小姐,让观众看到就行了。而在这出歌剧里,它从三个层面来讲述’旅程’,地理环境的旅程,音乐的旅程,精神层面的旅程,这里面蕴藏的精神能量让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跨界合作所产生的艺术碰撞,一次次的冲击着他对于自身和艺术的思考,也让他对昆曲艺术的思考日渐成熟。
“从根本上来,昆曲就是形而上的东西,它唱爱情,一定是要超越爱情的,它演人心,就要超越人心。《牡丹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用死来获得生,我活着得不到自由和爱情,得不到解放,我通过死来获得这一切;死的时候肉身没有了,反而精神能够永存,才真正追求到我要的爱情跟价值。从某种程度讲,昆曲也彻底改造了我,让我不仅看待爱情,甚至看待人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春江花月夜未央 生离死别不过误会一场
2015年,张军将唐朝诗篇《春江花月夜》搬上了昆曲舞台,一个用五十年坚守换来的“一眼万年”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年轻戏迷的关注,张军在其中饰演那个“一眼万年”的张若虚。“张若虚27岁就死了,但是他用50年的执念去坚守要见到的人,当他再一次见到她时,红颜已白发,唯江月恒长。罗周的这个剧本打动我的地方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它反映的是爱和时间的关系,看清楚生离死别原来不过是误会一场。”
《春江花月夜》是唐朝诗人张若虚的代表作,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千古绝唱。年轻的编剧罗周在拿到这首诗词的时候,并没有找到太多关于张若虚的历史记载,对于第一次创作昆曲剧本的罗周来说,这给了她极大的想象空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写出这种面对无限永恒的宇宙感?“我第一感觉他一定经历过生死,他一定从生到死这条非常狭窄的甬道走过。当他经历了无尽的忧伤和绝望,穿越了这一切之后,突然发现整个晴空灿烂,随之产生了一种唏嘘感,才会有这样的诗句。 ”基于这样的理解和情感基础,罗周写出了这场最终只能“长江送流水”、生不逢时的爱情故事。
“春江”首演三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这对于昆曲的“票房”来说,实属罕见。张军曾说,在上海,愿意为昆曲买票的观众,不会超过1000个。除了传统的戏迷、票友,这次来到剧院的新观众,全都是张军一场一场去“讲出来”的,光是为这出戏做的宣讲会,就开了20多场。
冥冥之中我的人生就被它塑造了
回到1994年,那时候的张军刚进入上海昆剧团工作,一场演出,台下只有几个观众,甚至舞台上的演员都比观众多。四年后,张军开始策划让昆曲走进校园的宣讲活动,他一次又一次的跟大学生讲什么是昆曲,什么是牡丹亭,昆曲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上千场的活动下来,跑遍了上海各大院校,也真的开始有年轻的观众走进昆曲的剧院,为数百年前的故事落泪。而在鼎盛时期,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制作的“水磨新调”音乐会在大学体育场演出,有三千名观众到场欣赏了这场昆曲表演。“现场热浪之高涨,我那时候才享受了一把,原来我们昆曲也是可以有’粉丝’的,至少说明昆曲是一个能够被大众接受的艺术。”
为了更好的让昆曲走进当代,他还通过与各种艺术门类的跨界合作来拓展昆曲传播的渠道。先后同华人音乐家谭盾、指挥家汤沐海,日本歌舞伎演员市川笑也、台湾歌手王力宏、英国小提琴家Charlie Siem、美国爵士大师Bobby McFerrin等艺术家合作,为昆曲获得年轻观众及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创造了可能性,也赋予了昆曲时代的活力。其中,由荷兰皇家歌剧院制作、谭盾作曲、张军主演的歌剧《马可·波罗》还获得2010年美国格莱美奖提名。
最近张军正在看一本关于日本浅利庆太和他的四季剧团的书,这是一个在日本戏剧史上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剧团,从一间小小的话剧社发展到日本最大的剧团,张军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向往:“那是我想要的剧团的样子。”
“你想要做更大?”“会会会,一定是啦,要做一个屹立不倒的老团。”张军说起民营院团面临的问题,已经听很多独立院团说过,没有完善的机制和成熟的体系来支持这样的发展。“它都是靠什么呢?靠某某某,比如说张军,挺愿意折腾的,也有一些资源,像王佩瑜也是,金星老师也是,都是靠创始人自己。在创业阶段你当然要靠个人,但最后它应该是个system,才能健康运行。”现在有这么多人跟着他一起做事,如果有一天他不干了,就是树倒猢狲散,这当然不是他想看到的。“大家都应该在这个团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建立起来一个机制,才有可能一直永续下去。即使我不做了,这整个摊子还能继续运转,这是让我很有企图的一件事儿。”
从一个被妈妈送去戏校的小毛孩儿,到舞台上的角儿,再到独当一面的艺术中心创办人,昆曲这种古老精细又脆弱的传统艺术,让一个人找到了生命的倚靠之力。从12岁进戏校,唱了几十年,张军曾经也怨过这个行当,“熬了多少年,我想要的成就感,我生活所需的一切,它都没有给过我,所以我怨过它,恨过它。”但今天的这个张军,大众口中的“昆曲王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等等头衔也都是昆曲赋予他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挺宿命的,冥冥之中我的人生就被它塑造了。”
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是需要你抛弃一切去勇敢追求的领悟到这点,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可以做到许多我原来无法想象的事情。”
最近十年,张军每周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项目——去声乐老师家练功。“我特别爱我的老师,姚士达先生,他真的是一个天才,他本身并不是什么音乐学院的教授。那时候文革动乱,很多戏曲演员十年没有唱戏,文革结束后,很多著名演员的嗓音都是被他抢救过来的。”
张军当年的老师叫计镇华,是昆曲界唱老生的第一把交椅,计镇华把张军送到姚士达面前,希望他调教一下这个有天赋的小孩子。“我从小嗓音条件很一般,一唱到最高潮就不行了,40分钟的戏唱到后面嗓子就哑了。但是我们传统昆曲训练都是靠模仿,老师只是说你学我的声音,但是发声是什么他不会教,没东西可教。”在姚老师那儿呆了一年多,张军还是没有开窍,“我觉得没用,那个东西学不会,他教的方法根本学不会”,也没有跟老师打一声招呼,张军就不去上课了。
半年后的一天,张军在阳台练功,顶着下巴在那儿唱,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的天,原来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怎么把某些关节控制住了,瞬间就开窍了,哎呀,太有意思了!”他重新回到姚老师跟前,讪讪地问:“老师,我再来上课好吗?” 姚老师把吸着的烟嘴放下来,看了他一眼,说:“每星期两节课。”
之后十年,张军每周都会去姚老师家上课,每次都是先陪他抽两根烟,喝五杯茶,然后开始训练,下课之后,姚老师都会讲起那些他已经讲了成千上万遍的故事。“对他来说,教学生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跟我们分享这些点滴是特别重要的。那些故事他都说了N遍了,但每次都说得兴致盎然,我也每次都饶有兴致地跟他呼应。”
2015年12月8号,这个日子,张军记得特别清楚,他那天状态不是很好,声带特别疲惫,而且在朱家角的演出也没有麦克风,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三个小时的戏唱下来,姚老师在后台等着张军,他说要回去写一篇日记,“因为今天是你里程碑式的一次演出。”唱段中有一个High E的音,以前张军唱到这句的时候,只要能够到达就算过关了,可那天非但到了,而且游刃有余,控制得非常好。“说明你的声乐力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所以我要把它记下来,今天既是你的日子,也是我的日子。”
“我非常爱我的老师,姚士达先生”

姚老师已经80好几了,但是看起来像一个50多岁的老人,精神倍儿棒,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身患癌症,且数次进出重症监护室的人,“他说他活着就是想告诉我们,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一直记得他跟我说,你不用去跟人解释,你解释再多,最后在台上是不是唱得够好,你的演唱是不是能够打动别人,你的演唱力量有没有到,这些才是关键,其他什么都是扯淡。你的演唱力量靠什么?你的气从哪里来?力量的源头在哪里?控制在哪里?他说这些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力量决定一切。”
夏天的时候,张军去老师家上课,姚老师打着赤膊在没有空调的家里练功,他说他年纪大了,力量开始消减,所以只有通过不停地训练来保持力量。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力量,是需要你抛弃一切去勇敢追求的。领悟到这件事,对我产生了质的改变,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可以做到许多我原来无法想象的事情。”
“活着获不得自由和爱情,获不得解脱,我通过死来获得这一切;死的时候我肉身没有了,但精神跟魂永在,才追求到真正的爱情跟价值”
M:你每一次在昆曲上的创新,都能兼顾自我艺术表达和观众感受,怎么抓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张军:一方面经典永远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我明年会做《长生殿》,洪升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爱情,我觉得跟汤显祖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管是我做《牡丹亭》、《长生殿》,《春江花月夜》还是《哈姆雷特》,都是不用再去跟大家解释太多的东西,经典是能够让大众都有感知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人有没有让我产生共鸣的地方。比如哈姆雷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跟我有一些类似的,他就是永远在强调自己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我做或者不做都是有我的理由的。
M: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张军:我对生死很感兴趣,这是我一直在说的观念。我们昆曲也演《红楼梦》,也演《梁祝》,但是我们未必能演得过越剧,越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欢女爱,对缠绵悱恻的刻画更加有力。那昆曲从根本上来讲是形而上的,唱得是爱情,一定是要超越爱情的,演人心,就是要超越人心,它有很多超越的东西,《牡丹亭》最伟大的是它用死来获得生。就是说我活着获不得自由和爱情,获不得解脱,我通过死来获得这一切;到死的时候我肉身没有了,但精神跟魂永在,才追求到真正的爱情跟价值。我觉得昆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个,这个剧种从某种意义上也改造了我,我看待很多事情,看待表演,会从这个角度出发。
M: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你在观念上逐渐成熟了?
张军:我大概是觉得,当我非常知道什么是感恩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更成熟一些。我刚辞职出来的时候说,原来待在体制里,演出是权力,可现在对我来说,演出是机会,这是本质的不同。以前团长不给我演杜丽娘,不给我演柳梦梅,我是要跟你吵架的,呵呵。
M:传统戏曲和年轻观众之间,一直是有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的,你怎么跨过这道“鸿沟”的?
张军:我觉得我一直保持着一种观众的心态,从来没觉得我是在庙堂里的,我高高在上。传统圈子里有这样的心态,觉得高雅艺术,你们又听不懂,要么自尊自大,要么特别自卑,觉得这种东西没人看了。我大概满接地气的是,这18年来我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们喜不喜欢你的东西,他们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其实跟生活走得很近、跟年轻人走得很近的话,会对我做什么有许多启发,这部分的我是很开放的,不是特别自我的。
M:你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障碍?觉得昆曲艺术就是阳春白雪的。
张军:从来没有。我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台下只有几个观众,我经历过非常惨痛而窘迫的时代,从我94年进入昆剧团工作到97年、98年,那四五年真的是一塌糊涂,真的,谁看昆曲啊,没人看的。所以当有很多人愿意来听我分享昆曲,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当然,艺术到后面会变得比较自我,当这些基础慢慢起来之后,我讲的观念会变得比较深层次,不再是说你今天觉得好看,我一定要给你变个脸。我觉得今天的人更关注自己生存的状态,他衣食富足了以后,他会想要去找一些文化上的源头,而昆曲里承载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这些东西是能够对话当下人的状态的。
M: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张军:不是,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是找不到根基的。我现在回头去看自己原来的生活,它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虽说也会做新的戏,但它整个逻辑是一成不变的。当然有的人是enjoy的,但偏偏我觉得这种状态不适合我,所以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我心里的这种声音比较强烈。
M:想要出来自己做?
张军:对,想要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然后有些事情就是不想再妥协了,这种妥协不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而是面对这个体制你不得不妥协。我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我演《牡丹亭》园林版,听我的新音乐演唱会,我们在演出中还结合了摇滚,他们就很感慨地说,老张你这个要是以前在团里,一个都做不了。以前的一些习惯和老观念吧,会在创作初期就把艺术家的激情和灵感全部抹灭消解掉了,但是我觉得艺术家的每一个冲动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很棒的艺术家被慢慢消磨掉,会觉得挺可惜的。

“水磨新调”新昆曲音乐会
“可能不圆满才能成全圆满吧?也是,所有东西都是被不圆满来印证的,圆满是多么得可贵,这真是,没错”
M:我今天看到你的第一感觉,不像我原本印象里传统戏曲人的感觉,怎么说呢,挺青春洋溢的。
张军:我以前是唱流行歌曲的,那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的,我当时接触到一个很严苛的唱片公司系统,对歌手上台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都有严格的训练和设定,这其实会让我反思我们昆曲艺术。我们以前说流行音乐不能跟昆曲比,昆曲多么高山仰止,可是你看人家流行音乐多么重视每一次跟观众的见面和交流,为什么我们昆曲的态度却是你爱看不看,爱听不听呢?后来我去交大读艺术管理,开始接触一些不同的知识结构,我才领悟到,你要把一样东西交给别人,是需要认真设计的,不是简单地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今天的人就能够感受得到。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我从观众中来,我其实知道他们的语言节奏,为他们多想一点,观众就一定会给出很好的反馈,这大概是我比较根深蒂固的观念。
M:你唱了那么多遍《牡丹亭》,演了那么多次柳梦梅,你怎么理解这个角色?
张军:其实汤显祖这个戏是写给杜丽娘的,像这样的戏,男演员心里要知足,这个戏70%是杜丽娘的,30%是柳梦梅的,你只要把你自己该干的事干干好就行啦,这个不能矫情。而且演完全部的柳梦梅,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挺世俗一哥们儿,在意功名利禄。现在大家看到的柳梦梅在“拾画叫画”那些特别痴情的部分,其实只是他的一个面向,我们没有展开来演这个人。其实“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说得是杜丽娘,不是柳梦梅。
M:所以在这部戏里汤显祖的个人寄托是放到杜丽娘这个角色上去呈现的?
张军:没错,像我现在在做的《春江花月夜》就是张若虚为主,简单来讲,他就是男版的杜丽娘。他在这个故事里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一个执念坚守了几十年,他怎么去理解时间,怎么去理解自己面对宇宙时的惆怅,这样的人才写得出《春江花月夜》这么隽永的诗。这个戏我演起来就是酣畅淋漓,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M:饰演张若虚会让你的感情观有变化吗?还是你也认为这样的感情只会存在于戏剧里。
张军:艺术是这样,虽然表演那部分只是表演,是一个表达出来的东西,它未必是真实的,但它对人心产生的刺激和震动是真实的,我觉得人一辈子坚守信念是了不得的事情,但人生总是遗憾的,你要接受这个遗憾。我以前自己做剧团也是吹毛求疵,但后来也因为演出这些角色,理解戏剧背后的意义,有些事情也能慢慢放下来一些了,应该放下来一些。
M:可能不圆满才能成全圆满吧。
张军:也是啦,也是啦,也是啦……所有东西都是被不圆满来印证的,圆满是多么得可贵,这真是,没错。
M:你希望大家想到张军的时候,会怎么评价这样一个艺术家?
张军:我只希望大家认可我是一个昆剧演员就可以了。我这一辈子的情愫也好,一辈子的爱也好,或者说是责任也好,我希望自己是个桥梁,能够架起传统戏曲跟这个时代的关联。如果以后大家说起昆曲还能记得我的话,我就会很欣慰,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吧。
“昆曲的根源一定是传统的,这一定是要坚守的,但是昆曲不能只有一种样子,它应该可以是多元的”
M:你觉得大家对昆曲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张军:听不懂,一说起昆曲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不懂,太阳春白雪了。
M:以你现在的理解来跟大家讲,什么是昆曲?你会怎么说?
张军:其实昆曲要一两句话要讲清楚,还蛮难的。这么说吧,昆曲是中国戏剧的源头,是百戏之祖,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集大成者,它涵盖的不仅仅是表演,还有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服装、空间……一切一切的集大成者,所以你看昆曲,会看到非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所以什么都比不上你来剧场亲自感受,因为剧场是一个魔力空间,太多东西都是无法从纸上、电视上感受到的,如果电视播昆曲,请你换频道,不要看,难看死了!那个空间感完全不对,它把最丑的部分给你反映出来。但现场是这样,你在我面前,我那水袖一挥,挥到你身边,像《牡丹亭》园林版,我在水里有倒影,风吹过来水会晃动,哇,你的感受马上就不一样了。也许你会没感觉,那是非常正常的,但也许你会有感觉,那这就是人生非常美妙的事,为什么不来试试?
M:“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愈发势弱了”,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是怎么想的?
张军:我们一说到传统文化所谓没落了,昆曲离我们现在越来越远了,就特别悲哀,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背负着毁灭传统的骂名,千万别,千万别。200多年前,昆曲、徽剧、汉剧结合产生的京剧,让老百姓更喜欢了,对我来说是悲哀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挺好啊,昆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该退出就退出吧。对我来讲,我愿意找知音,对别人来讲,他愿不愿意呼应我,这是因人而异的。我的理解是,别说昆曲了,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像《春江花月夜》做了20几次导赏,有的人会感慨昆曲的词怎么可以美成这样,我就说你看,这把钥匙今天就开了这扇窗了;那有些人看完以后说,我觉得还是动画片儿有意思,why not,那就选择你喜欢的。
M: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遗憾。
张军:我之前跟一个比利时的钢琴家合作过,尚·马龙,他现在是尚雯婕的音乐总监。我当时跟他合作的第一首曲子是我最爱的《懒画眉》——“月明云淡露华浓,欹枕愁听四壁蛩”。我就给他讲明代万历年间这个故事是啥样的,这段唱腔是什么情境,词意是什么,他能听得懂意思,但他完全感受不到那个情感。当然他的音乐出来会很有他的特点,但他永远抓不到这里面最最精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本身的母语就是这个,也许有一天你会有这个情致去感受什么是“月明云丹露华浓”。
M:你在不断尝试创新的时候,周围就有不断的维护传统的声音和争议,你自己会感觉拉扯吗?
张军:我们前年做当代昆曲周的时候,其中一个表演就是荣念曾老师带我们做的“一桌二椅”计划。演出结束后,我们做了一个演后谈,有年轻观众觉得这样的尝试很有意思,说他们经常看张军的戏,这次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有一个老阿姨就讲:“我要讲两句,我买了票是来听张军唱戏的,他今天站在那里20分钟一动都不动,你们在干什么?!我觉得你们就是在搞概念!”
M:哈哈哈哈,阿姨无法理解。
张军:我们就笑了,荣老师就很高兴的说,对对对,我们就是在搞概念,阿姨你看懂了。
M:你怎么说?
张军:那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在表演之前的思考过程,演出的当下和后面的座谈产生的很多讨论,这整个系统都是我们要做的这种戏剧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演出绝对不是个终端,我们大多数时候看一个演出都只是台上好不好看,没了。我自己这么多年下来的感受是,昆曲的根源一定是传统的,它本身的诗歌,曲牌体的意识形象,形而上的那些精神理念,这些一定是要坚守的,但是昆曲不能只有一种样子,它应该可以是多元的。其实荣老师做的先锋昆剧不会改变昆曲什么,只是让我们这些传统从业人员多一种思维模式,我一直讲离远一点也许会看得更清楚,可是我们常年身处这个界面里的人,受传统艺术训练出来的,通常它是不需要你去做思考的。
“张若虚到最后怎么能演呢?就一定是觉得盛唐的一切美好景象此刻都在我眼里了,然后看到这样一个女性,爱情就这么来了。如果这个人物不住在你心里,你是演不出来的”
M:你有没有过那种体验?就是某一句唱词你唱了很多年,突然在一个瞬间明白“原来它要说的是这个意思”。
张军:其实会吧,其实会的。一个表演者对情感的把控,对台词的领悟,要完全地在角色里面,才能诠释得好,你演是演不出来的。我记得葛优先生讲他的表演艺术,说镜头在前,导演叫action,你开始“演”,那你就演不出来了。像我就觉得张若虚到最后怎么能演呢?就一定是觉得盛唐的一切美好景象此刻都在我眼里了,然后看到这样一个女性,爱情就这么来了。最后张若虚看到辛夷已经老了的那个回眸凝视,那五秒种没有声音,那些瞬间,如果这个人物不住在你心里,你是演不出来的。
M:怎么让那个人“住在你心里”呢?或者说你怎么“活在那个人物”里?
张军:一方面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人文,都需要了解,要做很多功课。我做《春江花月夜》的前三个月都在做案头工作,有一天我开车出去,红绿灯都看不见了,就是看书看到假性近视。然后排练的时候又一遍遍地被击跨,找不到跟对手演员之间的感觉,找不到导演要的东西。后来我的小师妹来跟我说,师哥我看你最后彩排的时候,你的魂都不见了,你都不用演了,你就是张若虚。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全身心的沉浸在那个角色里,简直是疯了一样。
M:进入四十岁,你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张军:我特别谢谢跟我合作过的每一个人,包括在朱家角帮我们管理卫生的农民,你说他凭什么要尽心尽力,就为了那一点点劳务费吗?我觉得不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情感,是一个恩赐,要谢谢大家能够跟我在一起,就别再做错事了。如果说四十不惑,就是知道独木难成林,很多事要靠很多人一起来做才行。
M:会一直做下去?
张军:再做十年吧,教十年学生然后就该闪人了。唱到60岁吗?别了,别再麻烦大家了,老头儿了,扮相也没了。
M:现在年轻一辈的昆曲演员,是不是跟你们那时候也不一样了?
张军:我看到有几个学弟还真不错,状态很像韩国明星,小鲜肉,我就跟团里讲要爱护他们,多给他们一点机会,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昆曲难就在于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理解不了一些东西,只能按照老祖宗的戏依葫芦画瓢,没有能量去把握这个艺术形式,加上现在整个教育机制给年轻演员的空间也不是特别的好。
M:具体说说怎么不好?
张军:我们是这样,“6+4”,6年是中专,这6年没什么话讲,你什么都不要懂得,就是给我练功,练到“死”为止。像我们唱文戏的,跟头也翻得非常好,为什么?演柳梦梅翻什么跟头啊?可是你的脚伸出来,那勾脚面够不够漂亮,这些都是需要练功才能达到的“圆润”。但是现在的孩子不能责打,可是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唯有下苦功,没有窍门的。大学4年呢,就是在台上没完没了地演出,让你知道在台上气定神闲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上台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人家说你气场好,啥气场啊,那就是练出来的,练到你不怯场,练到你有超越自己身体的能量场。
M:你什么时候最爱自己?
张军:谢幕的时候,观众掌声如雷的时候,我是最爱自己的,特别有成就感。但是这些年,大多数时候是找不到这个平衡感的。唱文戏的人,不像翻跟斗,我今天哐当翻一下,底下掌声如雷,我们是得不到这种呼应的。所以我每次在台下做观众,看到演员谢幕的时候,观众啪啪啪啪地鼓掌,我都觉得好过瘾。”
采访完张军回来,这篇稿子写了很久,最终在数万字的素材里,摘出这么一片长文。跟朋友聊起,一个愿意在艺术里彻底沉浸的人,到底是什么留住了他?而且是昆曲,这么一个精细、唯美、脆弱、深情又千回百转的艺术,竟能够让男性表演者如此沉浸。
没有答案,无从得知。
敲完最后一个字,又在听张军在《水磨新调》那张专辑里唱的《懒画眉》,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唱段,真的好美,美得让人不愿再睁开眼戳破梦境。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一个人,若能在艺术或者什么里看见完美的人生化境,那便是一生的追求了吧?是男是女,有没有爱,根本不重要。那些让我们恒久有泪的东西,不思考,不挣扎,只会服从于它的安排。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